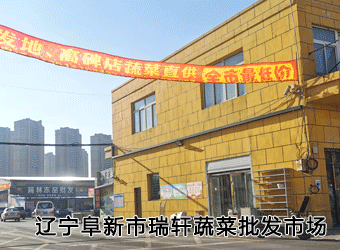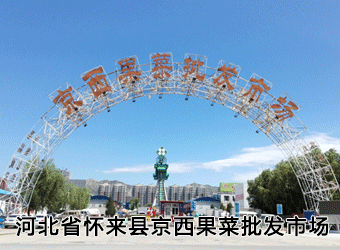"文化"为什么很难讲
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,中国学界对于“文化”有两种基本的态度,一种是不敢轻言文化,甚至一旦言及文化,就会不得要领而心惊肉跳;一种态度则恰恰相反,在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学的讨论中,再度大谈文化。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变迁、大讲民族文化复兴的新世纪岁月中,文化又成了“问题”,不得不再度浮上水面。一旦要讲社会、经济的发展,人们已经无法避开文化的建设等等相关问题。
当然,在这些方兴未艾的议论之中,讲论者内心也大都躁动着一种大致相同的意念,那就是文化实在不好把握。所以,在很多的场合,文化界和学术界就自然产生了一种文化“很难讲”的共识。
文化很难讲!
在此感叹之中,深藏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特别苦衷。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末,那种要以文化的变革来改造国家政治的气势,当下对于文化的讨论,的确会有一种隐隐约约“很难讲”的情愫。
关键的问题是,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,不好予以专业领域里的严格定义。其大者,文化可以包打天下,什么问题都可以囊括在其中;其小者,文化则深入人的精神内心、灵魂深处,见仁见智,容不得他人随便谈论。
如果关注它的人文定义方式,则其主观色彩太重,一旦进入个人的精神创造领域更是难以把握;如果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把握,则难以精神、价值等话语模式来表达。它需要数据、需要经验研究,常常要以制度的建构来取代旧有的文化讨论,以免“荆轲刺孔”的历史闹剧。
然而,文化——又不得不讲。民族文化、乡土文化、传统文化、都市文化、消费文化、世界文化……直至今天的和谐文化,又有哪一项议题之中,能够免谈文化?
一句“德参造化,灵通古今”,促使内圣者期待外王;一句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让中国人事事关心,常以天下、国家为己任。在中国人的“文化”概念里面,既有“文化天下”的神圣传统,亦有“文化革命”的风云激荡,继而还有“革命文化”的意识形态要求,最后还有当下“文化消费”的现代时尚。人人都在讲论“文化”,却难解其中三味,终得糊涂。
正可谓,日暮乡关何处是,精神落脚在哪里?
实际上,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、一种世界观、一个社区的守护方式,一种婚丧嫁娶的习俗、一种身份的界定的方法、一种看世界的方式、一种人际认同的方法、一种情感互动的符号。它始于人们与自己的乡土、村庄、家人、亲人联系的途径、而非只是天下、国家的合法性证明方式。
这个文化,也应当属于个人的,属于人们生活的社区,而非仅局限于国家、天下的,更非仅局限于君临天下、教化国家的传统“文化”。由此观之,文化还是不难讲的,还是可以谈论的。它的难讲,不仅仅是一个专业领域之中的定义问题,而且是一个以社会变迁、政治文明进化为语境的社会问题。
如果说,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话,那么,这就需要我们把文化置于社区、族群、人际互动模式、生活样式、民主制度……之中来加以考量,自觉地建构权力秩序与文化秩序之间的审美距离。曾经有学者提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,我认为首先就要在这个层面下工夫,在国家与市场之外,真正建构起空间化、社会化、制度化的文化自觉,把文化的讲求转换成为一种制度和社区的建构,演进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、人际互动的要求。不然,老是认为文化很难讲,天长日久,自然就损失了对文化的自信心。连讲文化的信心都没有了,还能讲求其他吗?
诚然,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捷径:文化很难讲,那就先做文化吧。
这可能是时下有许多人热衷于“做文化”,而不热衷于“讲文化”的一个缘故。做文化者,要比讲文化容易;因为文化消费,要比文化建设方便。传统中国人就有“知难行易”的说法。继续“做文化”,讳言“讲文化”,把“难”的东西暂时回避,先做那些容易做的事情。或者是,先把文化给消费了,消费得没有疑义了,我们再来讲文化。
来源:中国青年报(李向平)
当然,在这些方兴未艾的议论之中,讲论者内心也大都躁动着一种大致相同的意念,那就是文化实在不好把握。所以,在很多的场合,文化界和学术界就自然产生了一种文化“很难讲”的共识。
文化很难讲!
在此感叹之中,深藏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特别苦衷。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末,那种要以文化的变革来改造国家政治的气势,当下对于文化的讨论,的确会有一种隐隐约约“很难讲”的情愫。
关键的问题是,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,不好予以专业领域里的严格定义。其大者,文化可以包打天下,什么问题都可以囊括在其中;其小者,文化则深入人的精神内心、灵魂深处,见仁见智,容不得他人随便谈论。
如果关注它的人文定义方式,则其主观色彩太重,一旦进入个人的精神创造领域更是难以把握;如果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把握,则难以精神、价值等话语模式来表达。它需要数据、需要经验研究,常常要以制度的建构来取代旧有的文化讨论,以免“荆轲刺孔”的历史闹剧。
然而,文化——又不得不讲。民族文化、乡土文化、传统文化、都市文化、消费文化、世界文化……直至今天的和谐文化,又有哪一项议题之中,能够免谈文化?
一句“德参造化,灵通古今”,促使内圣者期待外王;一句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让中国人事事关心,常以天下、国家为己任。在中国人的“文化”概念里面,既有“文化天下”的神圣传统,亦有“文化革命”的风云激荡,继而还有“革命文化”的意识形态要求,最后还有当下“文化消费”的现代时尚。人人都在讲论“文化”,却难解其中三味,终得糊涂。
正可谓,日暮乡关何处是,精神落脚在哪里?
实际上,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、一种世界观、一个社区的守护方式,一种婚丧嫁娶的习俗、一种身份的界定的方法、一种看世界的方式、一种人际认同的方法、一种情感互动的符号。它始于人们与自己的乡土、村庄、家人、亲人联系的途径、而非只是天下、国家的合法性证明方式。
这个文化,也应当属于个人的,属于人们生活的社区,而非仅局限于国家、天下的,更非仅局限于君临天下、教化国家的传统“文化”。由此观之,文化还是不难讲的,还是可以谈论的。它的难讲,不仅仅是一个专业领域之中的定义问题,而且是一个以社会变迁、政治文明进化为语境的社会问题。
如果说,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话,那么,这就需要我们把文化置于社区、族群、人际互动模式、生活样式、民主制度……之中来加以考量,自觉地建构权力秩序与文化秩序之间的审美距离。曾经有学者提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,我认为首先就要在这个层面下工夫,在国家与市场之外,真正建构起空间化、社会化、制度化的文化自觉,把文化的讲求转换成为一种制度和社区的建构,演进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、人际互动的要求。不然,老是认为文化很难讲,天长日久,自然就损失了对文化的自信心。连讲文化的信心都没有了,还能讲求其他吗?
诚然,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捷径:文化很难讲,那就先做文化吧。
这可能是时下有许多人热衷于“做文化”,而不热衷于“讲文化”的一个缘故。做文化者,要比讲文化容易;因为文化消费,要比文化建设方便。传统中国人就有“知难行易”的说法。继续“做文化”,讳言“讲文化”,把“难”的东西暂时回避,先做那些容易做的事情。或者是,先把文化给消费了,消费得没有疑义了,我们再来讲文化。
来源:中国青年报(李向平)